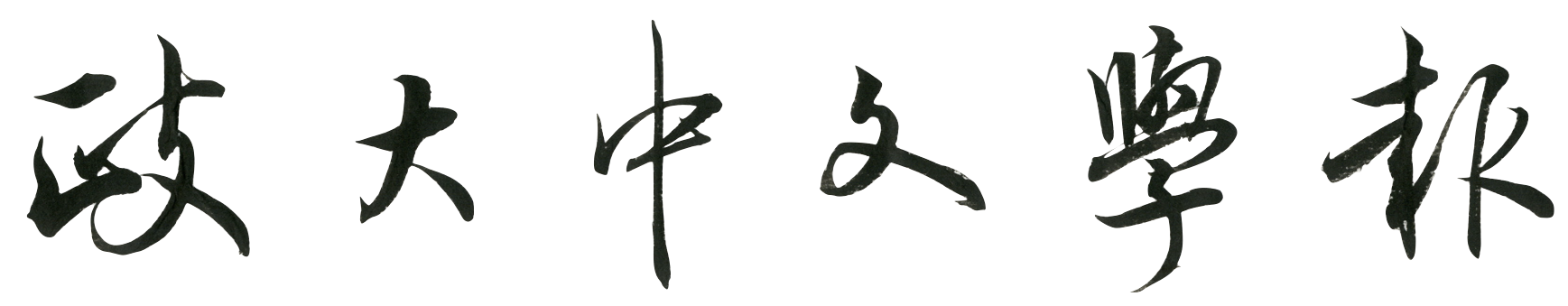-
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三期
出版日期: 2025-06
本文論近世「儒」的論說與變遷,從蒙元修撰《宋史》、滿清修撰《明史》皆於「儒林傳」外另立「道學」或「理學傳」談起,檢討諸儒的言論,以見明清儒學典範轉移的關鍵。筆者揭示「儒林」一詞,認為歷史上「儒」為一群體形成之社會階層,與時代升降相為表裡,故「儒」的身分設定,取決於群體自覺,以及群儒的治學內容。明末儒學衰微,肇因於儒者耽於「理」的討論導致知識嚴重貧乏,由此而引起儒者掀起的知識多元化運動,從文章、經史、經世等各類知識充實儒學,進而奠立清代儒學的基調。明清儒學典範性轉化,實受惠於晚明儒學衰微的刺激。故清代多元而充實的儒學開花結果,實得力於晚明儒學的花落腐土,化為春泥。
一般稿 唐李華文集流傳考
根據李華文集的流傳情況可知,李華文集在其辭世前後便得到了較為精心的整理,直至南宋年間,仍然以完整的形態流傳於世。李華在後世之評價,之所以略遜色於其本人在當年之地位,並非由於作品之存亡多寡,而在於其原本便處於承上啟下的文學史地位所導致的。
明清時期曾被視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第二次「百家爭鳴」階段。此時,除了儒釋道相互攻訐進行思想碰撞外,歐洲科學和神學的傳入也為中國帶來新的理論學說。這反映在當時的易學研究上,則表現為明清之際既有重視天道的「自然易學」和重視人道的「人文易學」,也有來華傳教士們重視「上帝」之道的「神學易學」。鑒於以往的學者們往往聚焦「自然易」和「人文易」的研究,而忽視「神學易」的形成、嬗變與影響,本文擬以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們對《周易》的理解和詮釋為中心,並揭示其理論背後的「神學優位」取向。
通過考察該時期利瑪竇、曾德昭、衛匡國、高一志、白晉和馬若瑟等人對《周易》的理解和詮釋,不難發現傳教士內部對《周易》有一個從否定排斥到肯定接納的轉變。明末的傳教士們排斥《周易》的根本原因在於「太極生兩儀」的宇宙創生主張同「上帝」創世相矛盾。因此他們將「太極」解讀為「第二性的」、「依賴者」,曲解「帝出乎震」的文本原意,堅持「神學優位」的詮釋立場。這引起晚明本土學者們的強烈反對,因此雙方圍繞以「上帝」和「太極」為中心的兩種宇宙創生模式進行了激烈的辯論。清初「索隱派」的傳教士則通過將《易經》定性為「東方的《聖經》」實現對《易經》「太極」創生宇宙圖式的認可。換言之,耶穌會士們在保持「上帝優位」的情況下,承認「上帝」創造《易經》而《易經》再造天地。
明清之際釋《易》所形成的「上帝優位」模式在海外易學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例如,被稱為英語世界易學發展史上的《舊約全書》和《新約全書》的《易經》譯本均帶有「神學優位」的翻譯取向和特徵。時至今日,仍然有英譯本《易經》保留了這種「神學優位取向」的翻譯習慣,如仍將「帝」翻譯為「God」。因此,作為海外易學源頭的「神學易學」模式值得被關注和研究。
在民初現代化的浪潮下,人們如何看待傳統端午節俗與端午紀念屈原的意義呢?由於報刊的盛行,我們得以直接考察民情輿論。筆者發現端午主題的文章大量集中於1918 至1929 年的上海報刊,於是本文第二節先梳理「端午專刊」的形成,說明它如何始於游戲場報,而後《申報•自由談》延續且擴大影響力,形成新型態的端午書寫。第三節探討端午之歷史傳說、衛生知識,以及游戲文章的內容與表現方式。第四節詮釋民初端午文章中頻繁出現的「三節收帳」、「新五毒」,體現了何種社會現象與心理。第五節則分析人們對於端午紀念屈原的看法,包含屈原的當代意義與自殺議題。整體而言,1920 年代的報刊端午文章,緊密扣合社會脈動,反映當時民眾的認知與情感,並藉由將傳統符號重新脈絡化,及詼諧幽默的筆觸,讓端午傳統融入新時代。
韓松《地鐵》以大量並陳中/西、傳統/現代、科學/志怪的手法,塑造帶有鬼魅性質的「幻境」與未來想像的「科幻境」。本文深入「地鐵」的「中間狀態」意象,和「怪異非常」所形構的「不確定性」,觀察韓松如何操作傳統/現代、物質/精神、形下/形上的辯證性質,形塑《地鐵》中後工業、後資本與後社會等多重意識形態變遷中的自我圖像。本文首先從「想像力的政治」,解釋韓松如何定義「鬼」的神祕性,將其視作中國文化想像力的本源;同時挖掘《地鐵》展現的志怪思維,及拼湊古典與多重文學資源的身體變異觀,觀察韓松如何營造科幻的陌生感,突顯「不確定性」的影響。其次分析《地鐵》的敘事時態和時間感知變化,探討文本經由時空混成所回顧的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。最後,本文試圖闡釋《地鐵》中的身體變異表現,及對資本主義和西方意識形態控制的抵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