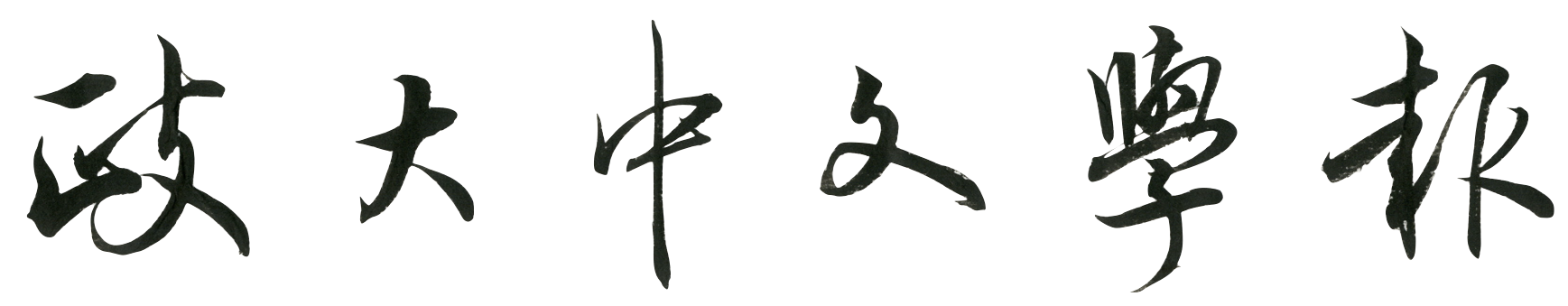-
政大中文学报 第四十三期
出版日期: 2025-06
本文论近世「儒」的论说与变迁,从蒙元修撰《宋史》、满清修撰《明史》皆于「儒林传」外另立「道学」或「理学传」谈起,检讨诸儒的言论,以见明清儒学典范转移的关键。笔者揭示「儒林」一词,认为历史上「儒」为一群体形成之社会阶层,与时代升降相为表里,故「儒」的身分设定,取决于群体自觉,以及群儒的治学内容。明末儒学衰微,肇因于儒者耽于「理」的讨论导致知识严重贫乏,由此而引起儒者掀起的知识多元化运动,从文章、经史、经世等各类知识充实儒学,进而奠立清代儒学的基调。明清儒学典范性转化,实受惠于晚明儒学衰微的刺激。故清代多元而充实的儒学开花结果,实得力于晚明儒学的花落腐土,化为春泥。
一般稿 唐李华文集流传考
根据李华文集的流传情况可知,李华文集在其辞世前后便得到了较为精心的整理,直至南宋年间,仍然以完整的形态流传于世。李华在后世之评价,之所以略逊色于其本人在当年之地位,并非由于作品之存亡多寡,而在于其原本便处于承上启下的文学史地位所导致的。
明清时期曾被视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第二次「百家争鸣」阶段。此时,除了儒释道相互攻讦进行思想碰撞外,欧洲科学和神学的传入也为中国带来新的理论学说。这反映在当时的易学研究上,则表现为明清之际既有重视天道的「自然易学」和重视人道的「人文易学」,也有来华传教士们重视「上帝」之道的「神学易学」。鉴于以往的学者们往往聚焦「自然易」和「人文易」的研究,而忽视「神学易」的形成、嬗变与影响,本文拟以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对《周易》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心,并揭示其理论背后的「神学优位」取向。
通过考察该时期利玛窦、曾德昭、卫匡国、高一志、白晋和马若瑟等人对《周易》的理解和诠释,不难发现传教士内部对《周易》有一个从否定排斥到肯定接纳的转变。明末的传教士们排斥《周易》的根本原因在于「太极生两仪」的宇宙创生主张同「上帝」创世相矛盾。因此他们将「太极」解读为「第二性的」、「依赖者」,曲解「帝出乎震」的文本原意,坚持「神学优位」的诠释立场。这引起晚明本土学者们的强烈反对,因此双方围绕以「上帝」和「太极」为中心的两种宇宙创生模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。清初「索隐派」的传教士则通过将《易经》定性为「东方的《圣经》」实现对《易经》「太极」创生宇宙图式的认可。换言之,耶稣会士们在保持「上帝优位」的情况下,承认「上帝」创造《易经》而《易经》再造天地。
明清之际释《易》所形成的「上帝优位」模式在海外易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,被称为英语世界易学发展史上的《旧约全书》和《新约全书》的《易经》译本均带有「神学优位」的翻译取向和特征。时至今日,仍然有英译本《易经》保留了这种「神学优位取向」的翻译习惯,如仍将「帝」翻译为「God」。因此,作为海外易学源头的「神学易学」模式值得被关注和研究。
在民初现代化的浪潮下,人们如何看待传统端午节俗与端午纪念屈原的意义呢?由于报刊的盛行,我们得以直接考察民情舆论。笔者发现端午主题的文章大量集中于1918 至1929 年的上海报刊,于是本文第二节先梳理「端午专刊」的形成,说明它如何始于游戏场报,而后《申报•自由谈》延续且扩大影响力,形成新型态的端午书写。第三节探讨端午之历史传说、卫生知识,以及游戏文章的内容与表现方式。第四节诠释民初端午文章中频繁出现的「三节收帐」、「新五毒」,体现了何种社会现象与心理。第五节则分析人们对于端午纪念屈原的看法,包含屈原的当代意义与自杀议题。整体而言,1920 年代的报刊端午文章,紧密扣合社会脉动,反映当时民众的认知与情感,并借由将传统符号重新脉络化,及诙谐幽默的笔触,让端午传统融入新时代。
韩松《地铁》以大量并陈中/西、传统/现代、科学/志怪的手法,塑造带有鬼魅性质的「幻境」与未来想像的「科幻境」。本文深入「地铁」的「中间状态」意象,和「怪异非常」所形构的「不确定性」,观察韩松如何操作传统/现代、物质/精神、形下/形上的辩证性质,形塑《地铁》中后工业、后资本与后社会等多重意识形态变迁中的自我图像。本文首先从「想像力的政治」,解释韩松如何定义「鬼」的神祕性,将其视作中国文化想像力的本源;同时挖掘《地铁》展现的志怪思维,及拼凑古典与多重文学资源的身体变异观,观察韩松如何营造科幻的陌生感,突显「不确定性」的影响。其次分析《地铁》的叙事时态和时间感知变化,探讨文本经由时空混成所回顾的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。最后,本文试图阐释《地铁》中的身体变异表现,及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控制的抵抗。